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公众号
中学化学教学参考公众号
张志春在评论中说,唐诗在学术界并非新话题,在当时及后世引发的言说层出不穷,而施蛰存先生的《唐诗百话》为何能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呢?就是因为他有自己特有的解诗模式,概括起来,就是“既入乎其内,又出乎其外”。通过张教授对“入乎其内”和“出乎其外”的详细解读,我们看到了作者施蛰存话说唐诗,既选编又辑佚,既考证又校勘,既笺注又诠释,既品评又赏析,推陈出新,别开生面。即便不一定完全认可施蛰存的解读考释,读者仍会欣喜地觉得早已烂熟的唐诗世界得到了刷新般地洗礼。
《唐诗百话》全书正文共100篇,上册收入“初唐诗话”“盛唐诗话”,中册收入“中唐诗话”,下册收入“晚唐诗话”和全书名词索引,并附录了施蛰存先生有关唐诗研究的文章若干,以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。全书有识见、有考据、有性情,被誉为“唐诗百科全书”。《唐诗百话》登上教育部与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“中国高校出版社书榜”2014年11月榜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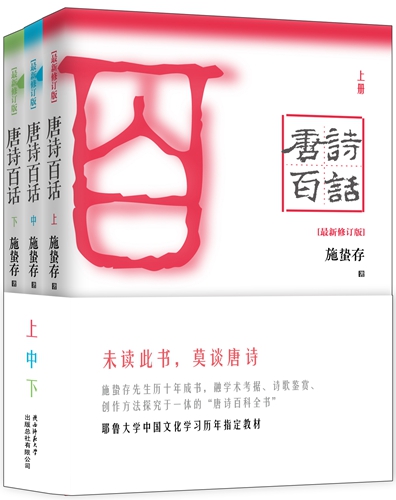
书评全文:
《唐诗百话》解诗模式论
——评施蛰存《唐诗百话》
张志春
《光明日报 》( 2015年1月11日 10 版)
作家、教授施蛰存沉寂文坛50年后撰著《唐诗百话》,自1987年问世起,就饮誉海内外。我们知道,唐诗在学术界并非新话题,在当时及后世引发的言说层出不穷,而施著何以能异军突起脱颖而出呢?我认为其解诗的特点是:既入乎其内,又出乎其外。
入乎其内
入乎其内首先是选题新颖。正由于作者能入乎其内,反复涵泳,对所选题材烂熟于心,意在笔先,所选内容使读者眼前一亮而充满期待。如讲白居易,讽喻诗不选《卖炭翁》而选《两朱阁》,感伤诗不选《长恨歌》、《琵琶行》而选《霓裳羽衣曲》;韩愈不选《早春》而选《落齿》;若所选众人愿选的,则点击其中所蕴含的唐诗历代疑难题迎难而上,道出自家凿凿有据的见解……,如此避熟就生,迎面立见陌生化的新鲜,便有弹射审美疲劳的张力。
入乎其内才能够文本细读。既品味整体,又细读诗题与字词句,使字词句篇乃至修辞格律一一打通,浑然一体。琢磨一个词汇、一个意象,诗人可能的特殊取义,考释诗歌题目导引诗思具体的趋向,整体把握诗境最深刻的意蕴。王之涣《凉州词》阅读一直有“黄河”与“黄沙”之辩,施蛰存既论句法气势,更论诗题诗句是谱唱凉州曲的歌辞,以为原本不专写凉州,何必一定要写黄沙呢?如此四两拨千斤,使漫长的蜗行摸索豁然开朗,去“黄沙”论者如釜底抽薪。如此核心部件的洞窥登时照亮了诗歌的整体境界。
入乎其内则更敢于以意逆志,与诗人对谈。施蛰存原是当代文学新感觉派开山作家,对于作家心态,创作动机,文本内在情感线索,情节脉络的领悟自有过人之处。他读诗敢对名家说褒贬,更有从内入手与诗人对谈的色彩与意味。如谈高适的《燕歌行》,从句法、韵法和平仄黏合角度看,以为实是七首绝句的缀合,每一首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,绝不与上下文联系,主题思想不一贯,从而导出历来选唐诗者随人高低对此诗盲评的新论。讲曹唐《小游仙诗》“藕花菱角满潭秋”时自注:“‘藕花’原作‘碧花’。‘碧’字与上句‘翠’字重复,实在不佳。今改作‘藕花’,好得多。我讲解唐诗而擅自改字,未免唐突。”在这里,品赏亦是创作,意在使前贤虚弱的字词或句子更为壮丽雅健。这恰是珍爱古人为其补足的盛意,亦是“齐民与俗流,贤者与变俱”意识在解诗中的体现。若联想到苏东坡颇多这类自铸伟辞的从容改削,解诗者自当会心一笑。
出乎其外
出乎其外,就是选取比较的方法。比较,就是选择更多的参照系,多层面多向度烛照诗人诗歌艺术的幽邃世界。其一如版本的比较考释。如白居易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,宋人删除“送别”二字,明人削掉“赋得古原”四字,蘅塘退士《唐诗三百首》不知此诗原题,逐句批点,误以诗名为《草》的核心意象指喻小人。施蛰存历时性比较中溯源纠谬,从而复原诗题,使诗歌原初本意立显出来。如此揭示事物原生态的文化启蒙,下大气力铲除芜杂的文化修复,在施著中不胜枚举。
其二如揭示人们容易忽略的背景。唐闺怨诗解读者多,而施蛰存则揭示易被忽略的府兵制背景,使诗意陡增。想想看,有唐一代,男子廿一入伍而六十退役,虽武则天改为廿五入伍,五十退役,了解这些,才会真切地知道,此时此地,此情此景,一个婚后无异与寡妇的女子内心的绝望与忧伤。
其三如意象的多重比较。王昌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,一般注家引鲍照“清如玉壶冰”为源,以为喻诗人对官场已冷淡如冰。而施蛰存放开眼界,考察姚崇的《冰壶赋》,继以王维、李白、陶翰、崔损、王季友、卢纶、韦应物等人所作的玉壶赋咏为证,意在说明玉壶冰的寓意是为官廉洁清正。在我看来,如此关键词的历时性考察,足以颠覆一诗的整体性境界。
其四如诗人诗歌的比较。如李商隐诗歌与宫体诗历时性比较,以为宫体诗思想内容不会越出文字意境之外,而李的艳情诗,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;与温庭筠共时性比较,以为无论意义还是价值,温的诗远不如李;再向后就李诗的影响延伸宋元明清历时性梳理,如西昆酬唱,如明前后七子,如清中期以后好作情诗专作无题……,可见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比李杜白等更壮观更绵长,影响力更大。如此交错而行,李商隐的诗歌史位置便显现出来。
其五是诗歌发展史诗歌运动的比较定位。施蛰存细读文本,考察唐诗的整个历程,提出了无论继承和发展方面“中唐诗盛于盛唐”的大胆新论。因为政治经济的盛唐与诗歌的盛唐不是全等关系。他选盛唐诗人十六家已觉再无可选,而中唐入选二十五家还觉割爱不少。“同样是五十三年,即使从诗人的数量而论,也可见中唐诗盛于盛唐。”这一阐释务陈言之既去,令人不由得重新审视这似乎早已定论的诗歌格局。
正因为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,作家兼学者施蛰存的十八般武艺得以充分地施展。他话说唐诗,既选编又辑佚,既考证又校勘,既笺注又诠释,既品评又赏析,更不用说作家介绍、作品研究、流派梳理、风格比较、创作经验探索、诗歌理论推敲等等都需推陈出新,别开生面。即如比较而言,也林林总总蔚为大观:如同意象叠加带来的蒙太奇效果,彼此相对呈现照亮对方,从而滋生新质。智慧的翅膀在唐代诗歌的宇宙间自在拍击;几十年的冷板凳在这里绽放出灿烂的人文之花;即便不一定完全认可施蛰存的解读考释,但人们仍会欣喜地觉得早已烂熟的唐诗世界得到了刷新般地洗礼。
(张志春,陕西师范大学教授。研究的重点为中国服饰文化、联语文化、民俗与非物质遗产和诗歌研究。)


 总社微信公众号
总社微信公众号 首阳云平台
首阳云平台